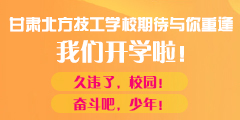当前位置:首页 > 正文
国家铁路局发布《铁路数字移动系统(GSM-R)设计规范》
近日,国家铁路局发布《铁路数字移动系统(GSM-R)设计规范》(TB 10088-2015),自2016年3月1日起实施。GSM-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自2006年在我国青藏线、大秦线、胶济线开通后,相继在京津城际、武广高铁、京沪高铁、哈大高铁等多条铁路线上开通运营,为运输调度指挥、列车控制及运营管理信息等提供了安全稳定的通信网络平台。
本规范是在《铁路GSM-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》(铁建设〔2007〕92号)基础上,认真总结我国GSM-R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,充分借鉴相关科研成果后编制而成的铁路工程建设行业标准,适应于高速、城际、重载、普速等不同等级的新建和改建铁路GSM-R系统工程设计。
甘肃轨道交通运输技工学校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,学校开设有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专业、铁道运输管理专业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专业、客车车辆检修专业、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专业等专业。
甘肃轨道交通运输技工学校北方校区
网址:http://www.bfgdyx.com
校址: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路890号
联系电话:400-689-0931,18089429846 QQ:2725865082
延伸阅读:
- ·兰州铁路局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纪实(2015-10-13)
- ·国家铁路局发布《绿色铁路评价标准》等3项铁路工程建设(2015-10-28)
- ·国家铁路局举办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培训班 (2015-11-05)
- ·购火车票无优惠 残疾人状告成都铁路局索赔3.15元(2015-11-05)
- ·昆明铁路局透露 沪昆高铁明年底前通车(2015-11-06)
热门专业 TOP6 MORE >

 电力机车运用与维修
电力机车运用与维修 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专业
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专业  幼儿教育专业
幼儿教育专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