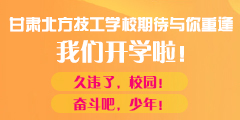甘肃高铁学校告诉你明年中职生怎么考大学!
本月初,
最后一次高职招考举行。
很多人在问:
明年还有高职招考吗?
高职招考是中职生考大学的主要渠道,
没有了高职招考,
中职生如何考大学?
甘肃高铁学校小编告诉你!
省教育厅昨日对外发布
《关于做好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》
简而言之:
明年有新的高职招考,
要考大学的中职生,
参加学考合格性考试后,
再考学考等级性考试!
来看详解↓↓↓
一中职学考分:
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
中职的学业水平考试(简称“学考”)分两种:
合格性考试
等级性考试
学考的合格性考试包括三个部分:
1.公共基础知识(含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计算机应用基础)
2.专业基础知识
3.专业技能考试
学考等级性考试包括:
公共基础知识中的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和专业基础知识
二哪些人要参加学考?
中职学考的考试对象如下:
2017年秋季以后入学的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在籍学生(含高职院校招收的中职学生)必须参加合格性考试,有升学意愿的学生还需参加等级性考试。
有升学意愿的2017年春季入学的中职学生需要参加合格性、等级性考试。
技工学校在校生和社会人员也可报名参加。
也就是说,明年中职生如果要考大学,必须参加中职学考的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,往届生也可以以社会人员身份报名参加。
三考试哪里出题?
那么,学考由哪里出题?
(一)公共基础知识、专业基础知识考试,由省里统一组织。
(二)专业技能考试由中职学校负责组织,学校应在每年10月底前将专业技能考试实施方案,报各市教育育局备案。鼓励有条件的设区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。
四考试内容是什么?
(一)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。
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计算机应用基础5门课程的考试内容,按照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德育等5门公共基础课考试大纲(试行)的通知》执行。
(二) 专业基础知识考试。
按专业进行,考试内容以教育部公布的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》为依据,每个专业指定1门考试课程(见链接),考试大纲由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编制后发布。
(三) 专业技能考试。
按专业进行,考试内容以教育部公布的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》为依据,由中职学校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。
五怎么考?
(一)公共基础知识考试
1.合格性考试。将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4门课程考试合并在一张试卷(公共基础知识综合卷I),采取书面闭卷笔试方式,考试时长90分钟。计算机应用基础考试采取上机考试方式,考试时长60分钟。
2.等级性考试。将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4门课程考试合并在一张试卷(公共基础知识综合卷Ⅱ),采取书面闭卷笔试方式,考试时长60分钟。与合格性考试分卷合场、一场考完。
(二)专业基础知识考试
1.合格性考试。使用专业基础知识卷I,采取书面闭卷笔试方式,考试时长90分钟。
2.等级性考试。使用专业基础知识卷Ⅱ,采取书面闭卷笔试方式,考试时长60分钟。与合格性考试分卷合场、一场考完。
(三) 专业技能考试。
专业技能合格性考试,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或应用信息化综合实训平台等方式进行,具体考试方式、考试时长由中职学校根据实际确定。
六什么时候考试?
公共基础知识考试(计算机应用基础)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;公共基础知识考试(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)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,专业技能考试安排在三年级上学期。
2018级专业基础知识考试仍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,2019级及以后专业基础知识考试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。
七怎么计分?
(一) 成绩评定
1.学考合格性考试这样计分:
公共基础知识综合卷I满分值200分,其中德育40分、语文60分、数学60分、英语40分;
公共基础知识(计算机应用基础)满分值100分。
专业基础知识卷I满分值150分。
专业技能满分值100分。
合格性考试各个科目根据原始成绩划定5个等级,由高到低分为A、B、C、D、E:
A等级约10%
B等级约35%
C等级约30%
D、E等级约25%,其中E等级为不合格、比例不超过5%。
合格性考试不合格的,由中职学校组织补考,补考通过的认定为D等级,仅用于毕业资格认定。
2.学考等级性考试这样计分:
公共基础知识综合卷Ⅱ满分值100分,其中德育20分、语文30分、数学30分、英语20分。
专业基础知识卷Ⅱ满分值100分。
延伸阅读
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学生,合格性考试各个科目成绩认定为A等级;
获得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、三等奖的学生,专业基础知识、专业技能合格性考试成绩认定为A等级;
获得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奖的学生,专业基础知识合格性考试成绩认定为B等级,专业技能合格性考试成绩认定为A等级。
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合格性考试成绩等级认定仅作为毕业依据。有升学意愿的技能大赛获奖学生仍需参加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,有关升学照顾政策另行通知。
(二)成绩使用
合格性考试成绩作为评估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重要依据,是学生毕业的依据之一。
从2020年开始,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后招收中职学生,文化素质考核使用中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,包括公共基础知识(德育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)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合格性考试、等级性考试成绩。
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后,高职院校招生专业面向的中职专业范围,参照教育部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(专科)专业目录(2015年)》(教职成〔2015〕10号)“高职专业衔接中职专业举例”及高职专业人才培养对中职专业基础的要求,由高职院校确定(另文公布)。中职学生专业基础知识考试成绩作为高职院校、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对应的中职专业学生的依据之一。
甘肃北方技工学校(华山教育集团·轨道交通运输学校)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,学校开设有铁道运营专业、国际邮轮专业、汽车工程专业、机电一体化专业、计算机应用专业、3D打印专业、学前教育专业、烹饪与酒店管理等专业。

学校代码:329
甘肃北方技工学校
华山教育集团·轨道交通运输学校
联系电话:400-1005-285
网址:http://www.bfgdyx.com
学校QQ:3051637108\\2764573068\\3069079425
校址: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文化宫华林路
延伸阅读:
- ·教育部“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会” 要求打造“名优土特产(2016-12-14)
- ·职业教育在海外(2016-12-14)
- ·甘肃: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甘肃召开会议(2016-12-14)
- ·全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将在贵州召开(2016-12-15)
- ·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重庆召开 研讨产教融合(2016-12-15)
相关热词搜索:甘肃高铁学校


 电力机车运用与维修
电力机车运用与维修 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专业
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专业  幼儿教育专业
幼儿教育专业